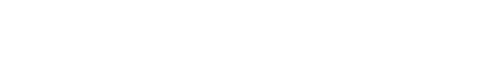张英进教授讲座:莎士比亚戏剧与早期中国电影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0-06-19浏览次数:10717
2010年5月18日下午,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张英进教授为上外研究生作了《翻译、改编、重写:莎士比亚戏剧与早期中国电影》的讲座。讲座由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査明建教授主持。
张教授以莎士比亚喜剧《维洛那二绅士》和由此剧改编的早期中国电影《一剪梅》为例,为听众展示了隐藏在戏剧和电影背后既有趣又深刻的文化意蕴。他首先将《维洛那二绅士》中朱丽娅的一段台词作为开场白,引出讲座的第一个问题:翻译背叛说。翻译者翻译了什么信息?背叛者背叛了谁的价值?早期研究翻译的学者认为译者应完全隐形,成为一个精准的传译机器,使译文绝对忠实于原文。操纵学派却把翻译看作一个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完全有可能与时俱进,在原文的基础上产生新文本。
接着,张教授谈到了电影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问题。由于论资排辈、仇视意象和亲逻各斯的缘故,电影改编长期遭人嗤之以鼻。如今,在电影改编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奈尔默提出了电影改编的三个关键比喻:翻译比喻、电影作者视角和互文比喻——三者分别代表忠实文本、依赖表演和变形生成其他文本这三个要素。
为了使听众更好地理解电影改编的问题,张教授引入了“撰者”的概念。由于文艺界面临着作者之死的危机,撰者作为一个机制,作为文本生产、传递和接受的环节,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原有作者的权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把“莎士比亚”也当成一个机制,认为他是书写、表演和销售等不同阶段的产物。
在厘清基本概念和观点的基础上,张教授以早期中国电影《一剪梅》为例,细致分析了这部电影改编的典型特征。《一剪梅》采用归化的手法,把《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两对情侣转化为名字本土化的沾亲带故的中国式情人,同时还采用三种手法加入了中国化的叙事:女性的男性化,民族主义情感的注入,梅花象征的装饰。其中,一度沦为土匪的男主角胡伦廷颇有梁山好汉遗风,擅长救苦济贫,相信女色误人,也算是极富中国特色了。《一剪梅》的改编也体现了文化混杂的特征,掺杂了美国冒险电影和罗宾汉式侠客的元素。明星的表演也使他们用身体的方式体现了文本。双语字幕,作为一种流转在陌生与熟悉之间的侵犯性字幕,增强了《一剪梅》跨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
最后,张教授总结,《一剪梅》的双语字幕同时实现了翻译中的归化和陌生化,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反而取得了双赢。根据帕森斯的“非零和”观点,翻译和改编上的“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原作的“失”,反之亦然。中国人把《维洛那二绅士》改编为《一剪梅》,既使莎翁名剧有了中国银幕版本,也承认、增加了莎士比亚的文学权威。
张教授结束演讲后,在座听众意犹未尽,纷纷提问,与张教授继续探讨有关“作者已死”、电影改编究竟应该忠于原作还是再创作、作者身份与权威应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张教授一一作答,还放映了《一剪梅》的片段,将听众带回了遥远的宛如梦幻的旧中国,体验到影片中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求,对家国的热忱。
张教授的讲座以轻松的视听享受为大家带来了学术上的启迪。也许按照张教授讲座中提到的“非零和”观点,学术的“得”并不一定意味着乐趣的“失”,这场讲座也同时实现了学术与娱乐的双赢。(研究生部 许原雪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