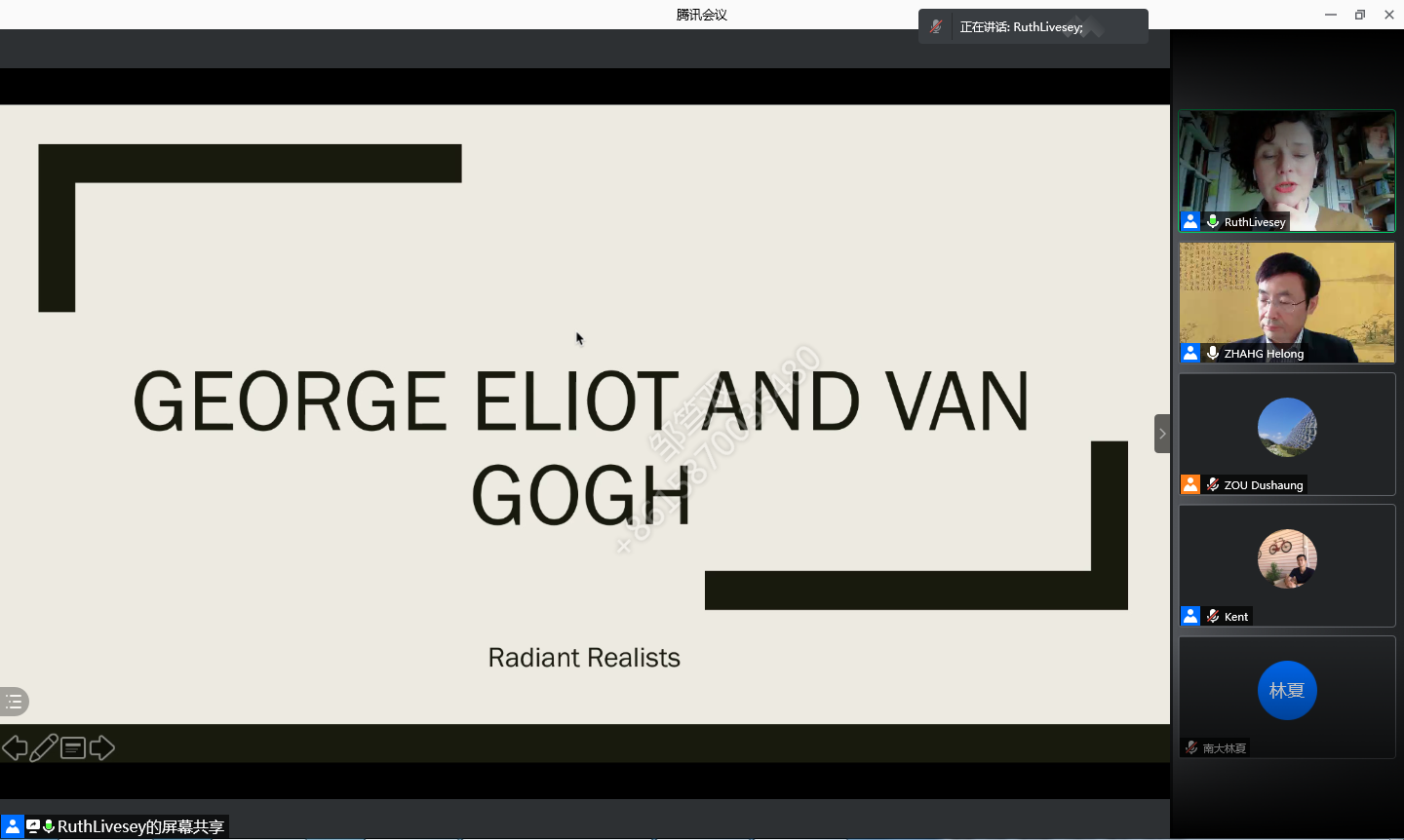5月25日下午,受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的邀请,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英文系Ruth Livesey教授通过腾讯线上会议,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George Eliot and Vincent Van Gogh: Radiant Realism”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文学研究院张和龙教授主持。
Livesey教授从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对梵高画作的影响谈起。她认为,梵高的画作通常被认为是通向20世纪那种世界性、实验性的现代主义的先锋;但艾略特却因其作品的乡村生活场景和“不远的过去”(recent ‘just’ past)这一时间设定,在英美学界被解读为一种保守的现实主义。然而在Livesey教授看来,梵高画作在形式和技巧上,均明显受到艾略特小说的美学形式影响。通过梵高讨论艾略特及其作品的书信,以及对梵高画作和艾略特小说文本的细读,Livesey教授为我们重新阐释了艾略特小说形式的意义:这种现实主义的乡村描写(realist provincialism)本身就具有一种激进的实验性,它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日常事务的认知方式,且促进了现代性的生发。
Livesey教授从两方面论证了梵高和艾略特在艺术形式上的共通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梵高对艾略特式的现实主义作出的“造型描述”(ekphrasis)。如果将ekphrasis理解为对视觉艺术的转述,Livesey教授使用此术语是为了再次强调艾略特小说形式——而非仅仅是内容和主题——的视觉性和艺术性及其对梵高的影响)。首先,色彩(colour)将艾略特同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区隔开来。后者指向一种单一色调(黑白)的社会现实主义,塑造出的是风格化的典型人物。梵高与艾略特均对这种类型化的思考方式和人物表征方式持怀疑态度。无论是梵高1885年的画作《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中年轻农妇对其丈夫“渴望而焦虑”的凝视,还是艾略特1859年小说《亚当·比德》(Adam Bede)中蒂娜·莫里斯对亚当·比德隐匿的爱慕,都对其时“农民”形象类型化的艺术表征——沉闷、操劳、单调——构成挑战,他/她们未言明的欲望和对自我内在欲望的意识,构成了乡村生活的色彩,并证明,具有欲望的主体并不应当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bourgeois individualism)所垄断。
叙述视角(perspective)是重估艾略特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对艾略特而言,普通大众和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美学类型,艺术的视角应当从神性下移到普通人。体现在叙述方式上,便是从全知视角转换到人物的主体视角。于是,视角成为一种共情方式(perspective as empathy),它将人物的成长、失败、救赎等主体经验,置放在此时此刻的当下和人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当中,以一种共时的整体性(synchronic totality)取代了线性的、进步的叙述观念。在一个逐渐世俗化的维多利亚时代,此种叙述形式不再指向一种浪漫主义的超验美学(transcendence),转而关注事物本身固有的内在价值(immanent significance),并强调普通人在一个宗教式微年代世俗的、此世的救赎方式:接受失败并开启第二次人生。
由于时间关系,Livesey教授未在演讲中对“视角”这一部分展开讨论。但是在问答环节,她就各位参会师生的提问,更充分地阐述了相关概念。以上关于“叙述视角”的总结正是基于演讲和问答两个环节,努力还原Livesey教授的观点。更加完整的论述可参考其发表在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杂志第29期的同名论文。这篇论文是其“Provincialism: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iddlenes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这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Provincialism: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iddlenes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 Research -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文/乔清泉)